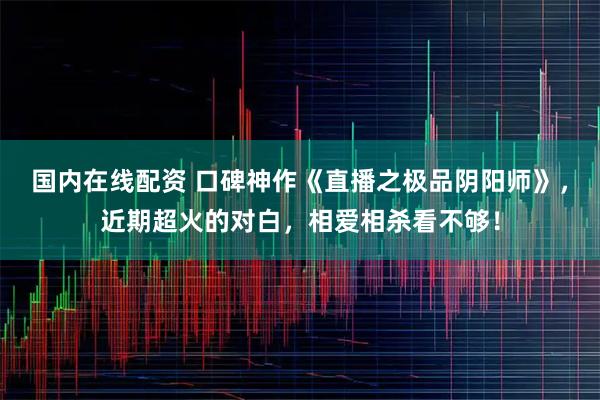1.
一九八八年的立秋,风里已经带了凉意。
如果你去过那一年的老城南,大概会在那棵歪脖子槐树下见过我。我戴着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住的墨镜,面前铺着一张画着八卦图的破布,手里盘着两枚并不值钱的核桃。
录音机里不知疲倦地放着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,那歌声火热,却暖不了我那颗死灰般的心。
我叫陈默,二十四岁。对外,我是个“开了天眼”却瞎了双眼的算命先生;对内,我是个被名牌大学退学、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丧家之犬。
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在这副墨镜后面躲躲藏藏,偷窥着这个世界的荒诞,直到那个叫林小婉的姑娘出现。
展开剩余92%她第一次来,是在下午两点。
那天阳光刺眼,我正透过墨镜的缝隙,盯着街对面理发店旋转的三色灯发呆。一双黑色的布鞋停在了我的卦摊前,鞋尖沾着点泥,却刷得很干净。
“先生,算命。”
声音很轻,像某种怕惊碎了什么东西的小兽。
我熟练地摆弄了一下手里的竹签筒,发出哗啦啦的声响,压低嗓音,装出一副老神在在的腔调:“问前程,还是问姻缘?”
“问命。”她说,“问我能不能活到这一年的冬天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透过墨镜下缘,我看到了她的样子。
那是那种放在人堆里绝不会被人多看一眼的姑娘。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,脖子上围着一条鲜红的纱巾,红得有些扎眼。她的脸很白,是那种不见血色的白,嘴唇有些干裂。
通常这种问生死的,要么是家里遭了难,要么是自己钻了牛角尖。
我叹了口气,开始了我那一套惯用的江湖切口:“姑娘,听你声音中气不足,但命宫有光……”
“我不听这些。”她打断了我,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“大团结”(十元人民币),轻轻压在我的八卦图上。
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十块钱。对于一个纺织厂女工来说,这可能是她半个月的伙食费。
“先生,你就给我算算,我要是活到了三十岁,是个什么光景?”
我愣了一下。那张钱上还带着她的体温,热得烫手。
我清了清嗓子,开始胡诌:“三十岁啊……那时候可是好年景。那时候咱们国家富强了,你也成家了。你住的是带电梯的楼房,不用自己烧煤球。你家里有个大彩电,彩色的,二十寸的。你爱人是个干部,疼你,下班就回来给你做饭……”
我一边编,一边透过墨镜偷瞄她的反应。
奇怪的是,她听得极其认真。那种认真,不像是听算命,倒像是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。她的眼睛亮晶晶的,双手紧紧绞着衣角,仿佛我说的每一个字,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砖瓦,正在她眼前盖起那座海市蜃楼。
“还有呢?”她急切地问,“那时候我穿什么衣服?我有孩子吗?”
“有,一儿一女,凑个‘好’字。”我信口开河,“你穿着……穿着那种大红色的呢子大衣,就像电影明星那样,站在大饭店门口切蛋糕。”
她笑了。
那个笑容,怎么形容呢?就像是干裂的土地上,突然开出了一朵花。那种满足感,让我这个骗子心里竟然生出一丝莫名的罪恶感。
“谢谢先生。”
那天她坐了整整半个小时,听我把她三十岁的生日宴从头盘却说到了甜点。临走时,她冲我深深鞠了一躬,那条红纱巾在风里飘了一下,像一团火。
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生意。
可没想到,从那天起,她天天来。
每天下午两点,雷打不动。有时候她带钱来,有时候带两个热乎的烤红薯,有时候是一瓶那个年代极珍贵的“健力宝”。
她总是那几个问题:“先生,再说一遍那个带电梯的房子长啥样?”“先生,深圳的大海真的是蓝色的吗?”“先生,我以后真的能坐飞机去北京看升旗吗?”
我就像个蹩脚的编剧,为了这一位唯一的观众,搜肠刮肚地把我在大学图书馆里看来的、对未来的憧憬,全都安在了她的身上。
但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
因为我发现了一些细节。
有一次,她在递给我烤红薯的时候,袖口滑落了一截。我看到她的小臂上,密密麻麻全是针孔,有的地方已经青紫了一大片。
我心里一惊,问她:“姑娘,手怎么了?”
她慌乱地拉下袖子,笑着说:“厂里干活不小心扎的,我是挡车工嘛,难免的。”
还有味道。
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味道。起初我以为是那个年代雪花膏的香味,后来混熟了,她离得近了,我才闻出来,那是一股廉价的郁美净混合着浓烈消毒水的味道。
那种味道,我在校医院里闻到过。
“你们厂卫生所的消毒水味儿挺大啊。”我试探着说。
她愣了一下,下意识地拽了拽那条红纱巾,把脖子捂得更严实了些:“是啊,最近……最近流感多,厂里天天消毒。”
那一刻,我隐约猜到了什么,但又不敢深想。我只是个躲在墨镜后面的懦夫,连自己的人生都烂成了一滩泥,哪有资格去管别人的闲事?
可是,人心都是肉长的。
随着深秋的到来,她的脸色越来越差,来得也越来越晚。有时候说几句话就要喘半天。但只要我一开始描述那个“美好的未来”,她的眼里就会重新燃起光亮。
“先生,你说我在深圳的海边,会捡到什么样的贝壳?”
“白色的,像玉一样,放在耳边能听到海浪声。”
“先生,你说那时候的电话,真的不用线连着吗?”
“真的,像个小盒子,哪怕隔着千山万水,也能听见声音。”
她听得入迷,常常忘了时间。而我,也在这日复一日的讲述中,仿佛找回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。
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,我不是被退学的陈默,她也不是满身针孔的女工。我们是一对在时光隧道里穿梭的旅人,拥有着无限的可能。
我甚至开始期待每天的下午两点。
我用她给的钱,去买了书,去买了报纸,只为了给那个故事增加更多真实的细节。我骗她说这都是我“算”出来的,她就信,笑得像个孩子。
直到冬至那天。
那天雪下得特别大,漫天皆白。街上的店铺早早就关了门,连理发店的三色灯都停了。
我裹着那件露着棉絮的军大衣,冻得瑟瑟发抖。我以为她今天不会来了。
可就在两点整,那个红色的身影又出现在了风雪里。
她今天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。那条红纱巾上落满了雪,像是一团快要熄灭的火。
她坐下来,喘了很久的气。
“先生,”她的声音很虚弱,比风雪声还轻,“今天是大日子,冬至大如年。你再给我算最后一次吧。”
“怎么是最后一次?”我心里莫名一慌,手里的核桃都忘了转,“你要出远门?”
“嗯,出远门。”她笑了笑,脸色苍白得几乎和雪地融为一体,“我要去个很远的地方。先生,你再给我讲讲,我八十岁的时候,是什么样?”
“八十岁……”我喉咙发紧,突然编不下去了。
看着她那双充满希冀却又黯淡无光的眼睛,我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崩塌了。
我不想再骗她了。
我想告诉她,没有什么带电梯的房子,没有什么不用线的电话,我也根本不会算命,我就是个连学籍都保不住的废物。我想带她去医院,哪怕花光我所有的积蓄,哪怕去工地扛水泥,我也想让她活下去,活在真实的世界里。
我颤抖着抬起手,摘下了一半墨镜,露出了那双完好却充满红血丝的眼睛。
“姑娘,别听了。”我的声音在发抖,“我骗你的。我其实看得见,我也算不准。那些未来……都是假的。”
风雪似乎在这一刻停滞了。
我不敢看她的眼睛,等待着她的愤怒,或者失望。
然而,一只冰凉的手轻轻伸过来,帮我把墨镜推了回去。
“戴上吧,怪冷的。”
她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心碎。
我猛地抬头,却看见她正以此生最温柔的目光看着我,嘴角挂着一丝凄美的笑。
“陈默,”她轻轻叫出了那个我隐藏了半年的名字,“我知道你是装的。”
我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,整个人僵在原地。
“你……”
“第一天你躲避那个骑自行车的孩子时,我就知道了。”她轻轻咳嗽了两声,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信封,放在那个画着八卦的破布上。
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
“因为我就是喜欢听你胡说八道啊。”她打断了我,眼泪顺着眼角滑落,滴在那个信封上,“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在你说的那个未来里,我有命去活。”
2.
她的话像一把钝刀,狠狠地锯过我的心脏。
什么叫“有命去活”?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她已经站起身,拍了拍身上的雪。
“先生,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那么好的梦。这个信封归你了,算是我预付的……下辈子的卦金。”
说完,她转身走进了漫天风雪里。
那个红色的背影,在苍茫的白色中显得那么单薄,那么决绝,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散。
“小婉!”
我喊了一声,想追上去,却因为腿蹲麻了,一个踉跄摔倒在雪地里。等我狼狈地爬起来,再抬头时,街道尽头空空荡荡,只有两行浅浅的脚印,迅速被新落下的雪覆盖。
那抹红色,不见了。
我发疯似地抓起那个信封,信封很厚,沉甸甸的。
我用颤抖的手撕开封口。
里面没有钱。
只有一沓剪报,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。
剪报的最上面一张,是一年前的一份《江城日报》。在报缝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,印着一则“退学通告”,上面黑白照片里的人,正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我——陈默。
原来,她早就认出我了。
我展开那封信,字迹清秀,却有些歪歪扭扭,显然是写得很吃力。
“陈默(原谅我知道你的名字,因为我在报纸上见过你写的诗,那时候我就把你当偶像了):
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
别难过,也别觉得在骗我。其实,我是个逃兵。医生说我得了骨癌,晚期,活不过三个月。我没听家里的话去化疗,因为我知道那是无底洞,我不想最后走得那么难看,还给家里留一屁股债。
我偷跑了出来,本来是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死。
那天走到槐树下,我一眼就认出了你。那个曾经在报纸上写过‘以笔为剑,刺破黑暗’的大才子,竟然戴着墨镜在装瞎子。
我觉得你好笑,又觉得你可怜。我们两个,一个是身体废了,一个是心废了。
我本来只想逗逗你,可当你第一次给我描绘那个‘三十岁’的时候,我突然不想死了。哪怕那是假的,可从你嘴里说出来,我就觉得那是真的。
这半年,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。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你的口才,其实是想买你的心气。
陈默,别躲在墨镜后面了。你有才华,你能看见光,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去活。替我去看看深圳的海,替我去坐坐飞机,替我……好好活下去。
落款:你的头号读者,林小婉。”
信纸从我手中滑落,掉在雪地里,瞬间被浸湿。
我跪在雪地里,发出一声压抑了许久的嘶吼。
原来这半年,我以为我在用谎言施舍她,其实是她在用生命供养我。
她哪里是傻,她是用自己最后的时间,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这个落魄才子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。她假装不知道我是装的,正如我假装不知道她快死了。
我们在1988年的风雪里,演了一出骗过岁月的戏,却谁也没能骗过命运。
“林小婉!你在哪!”
我疯了一样冲向纺织厂。
门卫大爷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:“林小婉?早就不在了!办了病退,听说住在市三院的临终关怀病房。”
市三院。
我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医院。那一刻,我不再是那个装瞎的算命先生,我是陈默,我是那个要去找回自己读者的作者。
冲进病房的时候,里面静得可怕。
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味,浓烈得让人窒息。
病床上,她静静地躺着,瘦得脱了相。那条红纱巾挂在床头,像一面垂落的旗帜。
医生正在收拾仪器,看到我闯进来,摇了摇头:“你是家属吗?来晚了,病人刚走。”
“不……不可能……”
我扑到床边,握住她那只已经开始变凉的手。那只手上,全是针孔,青紫交错。
她的眼睛半睁着,似乎还在望着门口的方向。
“小婉,我是陈默,我来了。”
我摘下那副该死的墨镜,狠狠摔在地上。镜片碎裂的声音,在空旷的病房里格外刺耳。
“你醒醒,我还要给你算命呢。我还没告诉你,九十岁的时候咱们干什么呢。”
我哽咽着,泪水大颗大颗地砸在她的手背上。
“九十岁的时候,咱们都老得走不动了。我就推着轮椅,带你去公园晒太阳。那时候啊,咱们国家真的有飞船上天了,咱们就在收音机里听……”
我拼命地讲着,讲那些我也没见过的未来,讲那些她最爱听的“胡说八道”。
可是,她再也不会眨着星星眼问我:“真的吗先生?”
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,发出刺耳的蜂鸣声。
医生过来拉我:“小伙子,节哀吧。她走得很安详,手里一直攥着这个。”
医生递给我一样东西。
那是两枚核桃。
我摆摊时手里盘的那两枚,不值钱的核桃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被她偷偷拿走了。
核桃被摩挲得油光发亮,而在核桃的缝隙里,塞着一张小纸条。
我颤抖着抠出来,上面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:
“你看,这世上原本不值钱的东西,被人放在手心里暖久了,也会发光。”
那一刻,我嚎啕大哭。
她说的不是核桃,是我。
3.
我是个被世界遗弃的废品,是她捡起了我,用她最后一点余温,把我暖热了,擦亮了,然后轻轻放回了这个世界。
1988年的冬天特别冷。
雪下了一整夜,盖住了老槐树下的算命摊,盖住了那条红纱巾走过的路,也盖住了所有的谎言与秘密。
后来,我真的去了深圳。
我看见了海,真的是蓝色的,浪花拍在礁石上,声音像极了她那天在雪地里的呼吸。
我也坐了飞机,在万米高空看云海,觉得离她特别近。
再后来,我重新拿起了笔。
我不再写那些愤世嫉俗的诗,我开始写故事。写市井,写人心,写那些在绝望中依然努力发出微光的人。我的笔名,叫“听风”。
因为她说,她喜欢听我胡说八道,就像听风一样自由。
三十年后。
我已经老了,头发花白。
我住在一个带电梯的楼房里,家里有个很大的液晶电视。虽然没有儿孙满堂,但我过得很安宁。
每年的冬至,我都会去老城南的那棵槐树下站一会儿。
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繁华的步行街,那棵歪脖子槐树也不在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喷泉广场。
但我总觉得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似乎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味道。
那是郁美净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,不好闻,却让我心安。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枚已经盘得玉化的核桃,轻轻转动。
“小婉啊,”我对着虚空,轻声说道,“现在的电话真的不用线了,大家都拿着个小方块,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对方。”
“现在的冬天也不冷了,屋里都有暖气。”
“还有啊,我现在不装瞎了。我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,虽然它还是有很多不如意,但我觉得,值得活一遭。”
风吹过广场的喷泉,卷起几片落叶。
恍惚间,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着工装、围着红纱巾的姑娘,正站在风雪里,歪着头冲我笑:
“先生,我知道你是装的,但我就是喜欢听你胡说八道。”
我笑了,眼角有些湿润。
在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,有些谎言,说着说着就成了真;有些人,走着走着就刻进了骨头里。
这世上最动听的话,从来不是预言,而是那句——
“我有命去活。”
哪怕只有一天,也要在爱与希望里炒股入门与技巧,活得热气腾腾。
发布于:湖北省同创内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